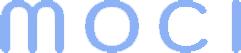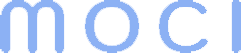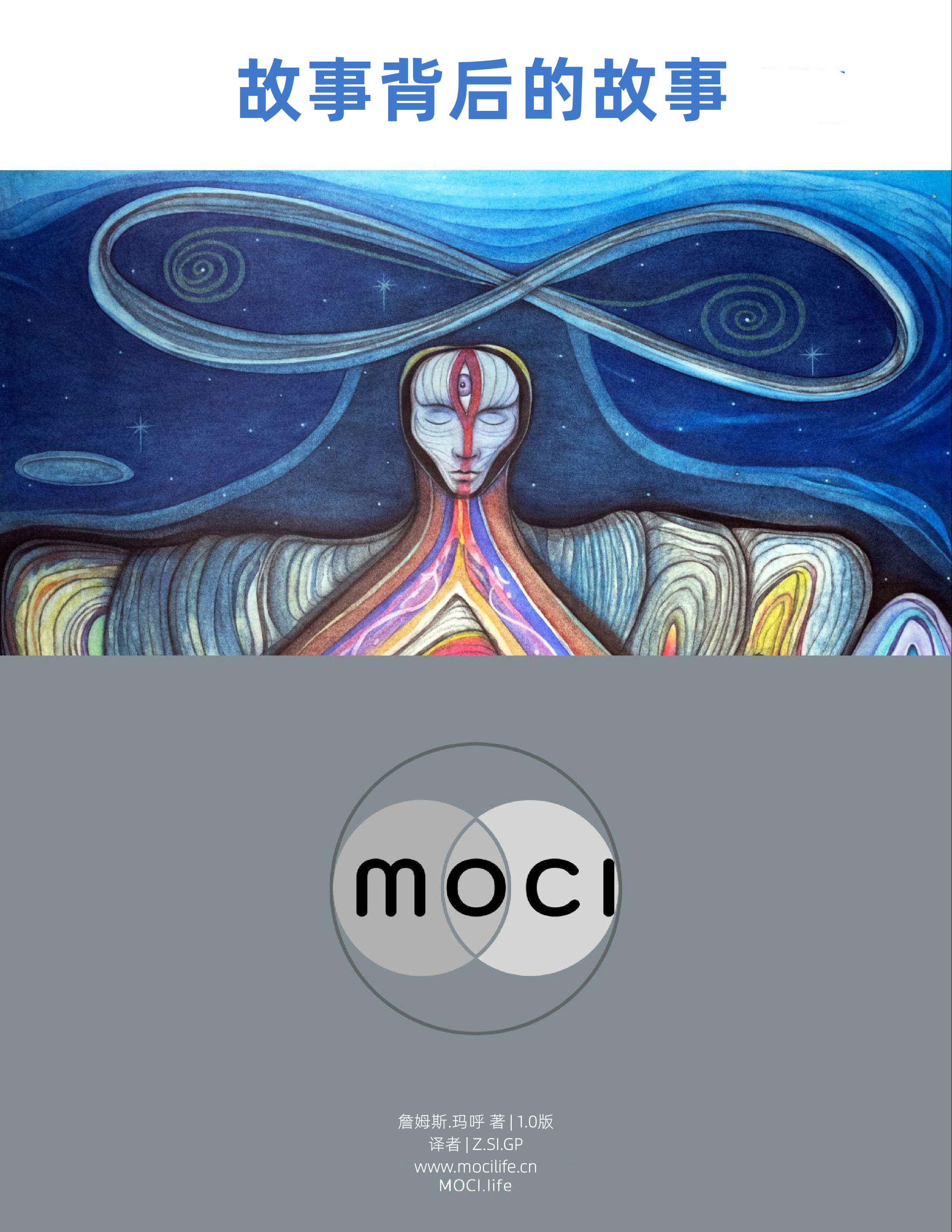故事背后的故事
源自最早的那些记忆,我相信自己是一名艺术家,尽管我无法界定会是什么类型的。11岁前后,我认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画家。然而,在大学学习艺术期间,我发现可以结合起我所热爱的视觉艺术、音乐、写作、诗歌、哲学,运用它们来共同地讲述一个故事。
那个时代,即便对于学者和梦想家们,“跨媒体故事讲述”都是一个陌生概念。影视制作是跨媒体故事讲述的典型代表。出于某种原因,对我而言,影视制作看上去太过事如其名。我想要某种更抽象的形式,来表达我头脑/心智中的主题。所以,我开启了一趟旅程,去创作一个当代神话,而这最终变得被知晓为了“造翼者”。
18岁左右,我开始构想这个神话宇宙应该如何地呈现。它将包含在一种故事讲述中,故事的展开会经由一系列小说,每一部都围绕着“主权性积分态”这个哲学概念;当“造翼者”(神话)完全确立后,我将写作一篇论文,来描绘这个内嵌于“造翼者”(神话)的核心哲学概念。这就是2021年以多种语言发表的《主权性积分态》论文。
在这个支撑性/包罗性的故事中,“主权体”是主角,“积分态”则是舞台,舞台之上,主角对抗着它的两个主要对手:时空二元性和文化性的分裂幻觉。主权体意识到,当作为单个生命期内的单体身份时,它所栖息的那个世界,仅仅只是一个“舞台”。真相则是,它实存于一种规模无限的时空二元性内,在其中,全部生命结合成一种智能与意志的融合物,运作得就如同受控于单一心智。
尽管单体身份——人类存在——沉迷于舞台,主权体却在观察、学习、进化着,这个过程伴随着主权体所辖人类生命的每一次迭代,实际上,是伴随着它所体验和表达的所有生命形态的每一次迭代。主权体意识并不只限于较高的生命形态,甚至不只限于地球。
这就是造翼者神话的关键,但跟所有神话一样,这个点也是不易理解的。它的传递经由了隐喻和事实虚构,这些可无法被表述为“真相”。表述“真相”就需要排出“虚假”的事物,可真正的“真相”却是:每一个事物都被互联着,都属于我称之为“积分态”的这个意识的一部分。逻辑上讲,在整体性中,并不存在真与假,仅仅只存在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。
主权体需要去“开垦”一直被它废弃的积分态,废弃是因为它总是低着头、睁大眼,凝视着时空二元性。正是在这样的时刻,主权体变得如此巧妙地分离出了自己的“积分态”自性,以至于变成了某个群体的一部分。变成了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中的“众体”的一部分。然而,存在于时空二元性内的“众体”之中时,人性部分变得知觉不到“个体”和“全体”——主权体和积分态。
我们的人性部分在基于相似性的网络中来形成关系。一种共享信念基于“幸存”而被形成。“幸存”是分裂性-思维。“我们”对立于“他们”。这些原则成为了我们的真理告知者。它们创造出了“众体”,可在潜意识里,经由直觉和想象,我们知晓主权体意识的存在,知晓主权体意识属于一个整体:积分态。
有时候,群体很小,比如家庭。其他时候,群体则规模巨大,乃至于整个国家。这两者之间,则存在着学校、宗 教、以及庞大等级制度中的其他人造组织,它们成为了我们的真理提供者,而我们则选择着,哪些真理共鸣于我们,哪些则不。不共鸣的要么被抛出舞台,要么被礼貌地分流向出口。它们遭到驱逐,这强化了我们那根本性的分裂感。
这个故事的主角处于这样的意识状态:意识的实存性横跨了时空二元性内的无数生命期,而意识则俯瞰着无限的时空,化身和学习着。我选择将这个意识称为主权体,主权体既是指“我”,也是指“我们”。这里的“我们”是指:主权体是其所辖各个生命期的混合物;“我”则是指单个生命期。
我们的身份是单个生命期,一个生活于21世纪初的人类存在,但这并非我们的真实本体。这是我们的时间性暂存身份。我们有着无限数量的时间性暂存身份,每一个背后都是主权体,“主权体”这个“我”,即是(上段提到的)“我们”。“我们”是一组“单体身份”——任何一个都存在于单个生命期内的80亿个片刻中;“我们”又是“一体”的,是我们曾经活过、正在活过、将会活过的全部生命形态及全部生命期的全部时刻的总和。我们拥有一个存在主义的本体,裂解于整体之外,又依旧是整体的一部分。
在这两种存在状态——主权体和积分态——之间,横亘着“众体”的等级制度。这是一条分裂之路,在其间,我们变得习惯去归属于一个群体,可能是家庭、宗教、种族、或是其他。
在我们时间性暂存身份的表面之下,我们的人性部分能够感知到主权性积分态意识。这在潜意识中完成着,就经由我们暂存身份中的各个激活点。这些激活点会(非预期地)出现在“众体”的等级制度内。通过生命中的这些点,我们能够转变方向,并感觉到扩张。一种正在回归我们天性自己的感觉,而且,曾经习得的所有适应性改变都被搁置一旁,以便展开一段全新的学习期。
无论等级制度内的真理讲述者们,如何延续或发展前辈们的信念和神话,我们都远不只是一种时间的产物。然而,我们对于该真相的知觉,却受阻于时空二元性和分裂文化,它们驱动着我们为了幸存的目的而在等级制度内寻求庇护。这就是“造翼者”神话的精髓,它提供了进入该真相的多重视角,大宇宙的诸世界、灵性哲学、抽象的超现实主义美术、音乐、诗歌、故事讲述。
18岁时,我并未立即掌握这个故事的全部细节。细节们总是在我需要它们时才来到。我是一个故事讲述者,编织着关于主权体的故事,以及在时空二元性的舞台之上,人类生命的有限跨度之内,主权体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主权性积分态。艺术是该故事不可或缺的部分,因为艺术能够表现出这种意识,并在地球上给予它一种象征性的描绘。
另一方面,科学正奋力去看入这些非物质的、超自然的世界,它们远远超出于我们世界之外,超出了我们舞台之外,让我们无法相信它们,除非是基于宗 教神话或药源体验,而短暂探入它们的回声中。科学仪器是基于我们的舞台而构造的,它们又怎么可能望向舞台之外?现在还没有“望远镜”能望出我们的物质性“舞台”之外。
对于“超维度望远镜”的构建,科学界的态度暧昧不明,即便那镜头仅仅只是纯粹的数学。数学将尝试创造出一系列强大的数字,简单到几乎任何人都能通过一段文字而明白它的含义。然而,那仍旧是一套数字和符号,太过抽象而无法获得体验,进而无法带来理解,从而也无法进入意识。
数学不是意识。它是一个看入意识结构的镜头。它就像“超维度望远镜”的镜头,看到了一个独一无二意识的可能结构,并能做出假设:该意识可能被互联着其他意识。主权体意识要被体验,无法通过科学、数学、宗 教、信仰、毒 品、公式、咒语、冥想、或书籍。存在于人类性中时,对它的体验,被保留给了我们的想象力和直觉。这2者就“寄存”在我们的更高头脑/心智和心脏中,然后被带到我们生命的表层来作为激活点。
宗 教、哲学和灵性创造了神话,来描述那超出我们共同创造出的舞台之外的事物。科学和数学通过仪器和严谨的理性,正在做同样的事。事实上,这两个领域的每个人都参与进了关于我们起源的自我-探索。他们就像分别始于山的不同侧来挖掘一条隧道,在显意识知觉之下,他们正计划着如何在途中某处相遇。唯一的真正问题是,相遇是初试即达成,还是需要后续数量未知的更多尝试?
当我开始作画,几年之后,我发现了“哲学”,这是一个缓慢的体认过程,我体认到了那些儿时就理解,但缺乏表达手段来清晰表述的事物。我不得不发明一些概念,像是“主权性积分态”和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,只因为这些并未被收录进我所读过的宗 教、哲学或灵性书籍。
接着,我将这些概念翻译成艺术、音乐、诗歌、绘画和故事,这些就变成了主权体在我的世界里穿着的“衣服”。我决定分享我的故事,则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任何类似于它的。我推测,自己的匿名作品会保持为小众,低调,仅仅经由他人传播,但我也知道,经由他人,它能够生长,而且是全球性地生长。
我想强调的是,我只是一个个体,一个故事讲述者,想要鼓励人们去思考自己那超越了单个身体、单个生命期、单个名字的身份。这个行星拥有近80亿人口、700多种不同语言和4000种宗 教,很难去真正地理解,我们在物种层面是作为一个集体意识而存在和生活的。
挑战就在于如何讲述如此宏大的故事,又不让人们迷失方向。我的答案是:通过“跨媒体”来艺术性地讲述,跨媒体提供了不同的门,一个人可以穿过它们进、出故事;并不去试图讲述宏大故事,而是去讲述最微小、最个人化的故事,容许读者的头脑/心智与心脏被投入到并不专属主角的故事中。
通过艺术养活自己的艺术家,通常会转变自己的艺术去引发特定市场的兴趣,并响应该市场的规模、趋势线、关联性、以及对艺术家愿景的尖锐评判。“主权性积分态”的艺术并不意图引发任何人的兴趣。相反,它的目的是搭档于暂存身份——单个生命期的人性部分——将其牵引向其艺术本身,它就仿佛一位母亲,在将孩子搂进怀里。它就像在以“无限性”和“全体性”来增强暂存身份。
仅仅一点点微光就能开启这扇门。一旦门打开,我们就能将它开得更大,主权体将进入,暂存身份也将进入,正是这种情况达成了主权性积分态意识。2者将逐渐结合。2者将变成“我们”,一种搭档关系就此诞生。
在这个场境中,所有那些圣人、救世主、天使会出现在哪儿?科学家和数学家会出现在哪儿?所有的哲学家和灵性老师会出现在哪儿?他们全都留在等级制度中。留在“众体”中。他们是向暂存身份讲述暂存真理的人。他们是桥梁,跨接起了主权体与积分态、个体与全体。
他们是美丽的桥梁——群体意识的马赛克画。他们是接口界面,我们能运用来勘探更远的世界。然而,在某个时点,我们将穿越这座桥,我们将看到桥的本来所是,再不担心它的消失,因为,我们是一个整体的必不可少的积分性部分,而我们清楚这一点。这种知晓完全不依赖实际经验。我们仅仅就是知道!我们需要的全部只是一种表达手段。一种以想象力去看到它的方式,一种以直觉去感觉到它的方式。
艺术是我们的表达手段。科学和数学也是。艺术会表现出那非感官证据。这证据被持有在我们的最深核心处,能够被我们的最高心脏感觉到,被我们的最高心智/头脑所理解。但并不完全。对真理证据的追求,是一种分形化的渴望,永远无法被彻底满足。然而,我们却能够将非感官证明灌注进我们的创造物,表达进我们的品行中。
运作于对全体友善和慈悲的原则时,我们就会发现重要之事。重要的不是“证据”上的开疆拓土。重要的是品行——将我们暂存身份的暂存创造物共享给了全体。
我创作了无数的笔触、键击、音符和文字。每一个都需要时间,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次生命期,至少是一次生命期的重要部分。我一直明白,艺术家的道路是孤独的,因为艺术创造出自独处。为了去理解主权体,并为它发声,我需要感受主权体在我内里的振动,否则,就没人会相信,我所知晓之物超出了他们的已知范畴。既然那样,又何必去听千篇一律的东西呢?
主权体的故事是一个入口通道,通往一种界定我们自己的新方式,故事作者是个微不足道的人——事实上可以是任何人。只是碰巧是我们罢了。我并不将我创作的任何东西视为自己的,因为当我深入这个故事时,我意识到它是属于“我们的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视角,去发现我们的身份和目的:如何将非感官证据具体体现进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呼吸、我们跳动的心脏、我们所有的人性部分。
造翼者和MOCI是一对翅膀,讲述着同一个故事:主权性积分态,我称之为SOIN。这种意识是如此浩瀚,以至于它变得隐而不见——这种智能的规模和类型都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。任何给它穿上衣服的尝试都会带来有价值的理解,但都不足以达成整体的理解,“不可知”就运动于整体中,并于此拥有了它的存在性。这就像“哥德尔不完备理论”,真理无法被证实。不只是因为它一直在无限地进化,更是因为真理只能被发现于主权性积分态意识内,而身为人类时,我们又不知道如何去体验这个。
所有故事都存在一趟进入其间的旅程,也存在一趟离开的旅程。进入时,我们不知道该期待些什么。探索这个故事时,我们也许会感受到一种共鸣,共鸣于某种根本性的但却被我们忘记的事物——我们一直知道它,但没有话语来描述。它的价值或许最初并不明显,但最终,一个故事将浮现出来,它如此宏大,足以开启一种可能性,那就是:我们被互联于遍布全部时空的全部物种的各种生命形式。
幸存和分裂已经掩藏起了这个故事,并非故意的,那只是它们固有设计的一种结果。然而,意义,就存在于这个(隐藏)故事的情节弧光中,而非我们的现实时刻里。作为人类,按时空二元性计,我们大略会在一具暂存身体内存活约25亿秒或片刻。而那横跨于各生命期、各时空、及分形化实相中的本体,将经由我们浮现进这个世界。这就是被嵌入这个故事中的充满希望的意义。
人类正在接近天命的岔路,在那儿,我们的技术能够界定出我们的命运,而不只是启动它。这是一个关键时刻,因为,技术能被用以增长我们的分裂感,也能用以提升我们对“互联”的体验和理解。正如任何人能想象到的,这2条道路所引发的人类品行可能是截然不同的。
在我看来,这就是为什么,在这个时代去理解“主权性积分态”如此之重要——这就是为什么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正在浮出到我们世界的表面。我们在被引导向这个根本性的哲学结构,即:在一个平衡点上,我们同时是主权体和积分态。我们最高的心脏和头脑/心智就像助产士,助产着这种“体认”进入我们的生命,来作为“意识与互联”的代理人。
这种体认的提出不是作为一个感官证据,而比较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延伸,延展那意欲理解“整体”的集体意愿。每个物种都在自身的暂存实相中做着这事。这件事并不属于宗 教、灵性道路、科学理论、甚至逻辑推理。它属于一个不同的秩序结构,该秩序结构同时存在于时空之内和之外。“时空之外”不是指,还存在“非空间”和“非时间”,“时空之外”是一种完全不同于“时空”的秩序结构,能够实现维度的折叠/包纳,在“时空之外”,“个体”变成了“全体”,因而,“全体”也能够变成“个体”。
“全体”无法分离于“个体”而独存。2者天生就必然同时存在,也就是说,一旦发现自己是主权体,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是积分态。时空作为一个物理过程,容许了这种体认在整个浩瀚的时空中缓慢而笨拙地浮现出来。正是时空,产出了富饶的体验和表达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穿越广大的时间跨度来进化。
作为个体,我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主权性积分态体验的吸引。然而,无论我们获得该种体验到何种程度,那都是我们的价值观在特定时空的一种反映。如果这种体验来得过急,我们与人类现实实相的接口界面就可能被损坏。当这体验在平衡中被达成时,我们与人类现实实相的接口界面就会被增强,因为我们把每一个事物都视为是:一个天性自己,正在如其所愿地收获着他们的体验,并表达出他们自己。
“存在体”的这种秩序结构正是我们的天然状态。它的出现需要主权体和积分态这2个状态创造出了一种有意识的搭档关系,正是在这之后,所有的学习都变成了“个体”向“全体”及“全体”向“个体”的充分交互。我们存在性中的其余所有状态都是被适应性改编的。所谓适应性改编,就是我们天然状态受到了一种时空形体的“污染”,(因为)这些时空没有能力折叠/包纳起各个维度。这些时空,一旦致密化为物质,就创造了更强的分裂和剥夺感,分裂出我们的天性自己,并剥夺了我们去看到全体生命的天性自己的能力。
写作、绘画、作曲的艺术,是的,甚至数学,都揭示出了一个镜头,以允许我们看到“主权性积分态意识”的回声和影子。如果在我们选择的岔路上,技术是作为一种赋能力量,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天然的“互联性”,那么,我们就能将“互联”锚定于人类物种内。我们就成了带有这份理解的管理员,并能互联上其他生命。
这就是爱之新形式的诞生方式。这种形式的爱并不专属于某个物种,某个行星,某个命运。这种爱带有一个目的。这种爱的根即对于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的理解。而这才是真正要紧的。如果爱没有包含这种理解,它就缺失了核心。如果核心缺位,在追寻非感官证据的道路上,即便想要获至主权性积分态意识,找到的依然仅仅只是影子。这是因为,我们并非悬浮在冰冷虚空中的数字。我们是振动性的轮毂,辐条则是进化中的头脑/心智与心脏的集合,它们所属于的演化进程,是隐藏于语言或数字之外的。
一次揭示的背后,永远还存在着更多。更深之物总是存在着。我们身处一趟旅程的中段,旅程目的地则因为时空及“众体”等级制度的分心而被忽视了。这趟旅程的刹车是文化性的分裂幻觉,加速器则是对“互联”的理解。
我们全体,分工合作地,在我们的旅行中,运用着刹车和加速器来保持着平衡。“全体”的进化之旅,单纯只是太过浩瀚,因而无法拥有一个愿景,甚或无法去探测它的总体性目的。如果能够概括,并落实成语言,我会假设,它的目的也许就是创造出一种更高的和谐,而方式即是去理解“我们之是谁”:我们是拥有单个生命的个体,我们是下辖无限生命的主权体,我们是整合于“全体”的积分态,而且,我们将这些身份校准为了搭档关系,即便我们还不理解它们的总体性或终极目的。
就我对这个故事深度的挖掘而言,在一次暂存的生命期中,我们依然保有着另一个身份,我们的天性自己,它被体验和表达所锻造着,并被永远地编码在我们的主权体内。我们的天性自己并未溶解进大自然或“全体性”中。相反,它存在为了主权体(分形化的天性自己)和积分态,并跳跃于这2种秩序结构之间,永远在基于对侧实相来教导和学习本侧实相,从而获得更深的洞见,更广的视野。
对我们中的一些人而言,是时候展开自我教育,移除掉自己那适应性改编的时空二元性接口界面了。是时候解开“分裂”的枷锁,挣脱掉“分裂”对于历史——我们个人的及全人类的历史——的顽固监禁了。是时候担负起“元-意识”管理员的责任,“元-意识”永远都需要有人来扮演未来探测者和过往疗愈者。